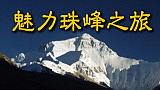朝圣慕士塔格调
朝圣慕士塔格 迟来的讲述
我第一次登雪山就选择了海拨7546米的慕士塔格,而且居然成功地登顶了,全队13名队员都登顶了。不要因此就认为慕士塔格是一座多么容易攀登的山峰。从图片上看,慕士塔格是一条平缓的渐开线形状的大雪坡,其实那只是视觉效果,是山体的外轮廓线,在这条外轮廓线下还隐藏着许多复盖着厚厚积雪的沟谷和较陡的雪坡,尽管这里不需要什么攀登技术,但也很少有人认为登顶是轻松的。我们能成功也是多种因素的合成结果。首先是今年天气好,从我们7月15日到达大本营到8月4日离开大本营总共21天,山上没几天坏天气,据说往年可不是这样,而且山上的雪要比今年厚得多。其次我们参加的是乌鲁木齐市登山协会组织的商业登山活动。我们这样选择,就是为了用金钱来换取高成功率。参加商业登山活动的费用要比自助登山高得多,除了可以挥金如土的人,谁能不仔细审视一下自己的实力再作决定呢?比如说我吧,那也是因为以前曾到过珠穆朗玛峰5800米处没有任何高山反应才大着胆子下这个决心的。其他多数人都有过多次登雪山的经历。
我们这支队伍共有18人。领队杨春风,副领队宋玉江,大本营总管兼厨师1人,还从西藏登山学校请来高山协作2人,普布顿珠和索玛旺青。13名队员中四川4人、深圳3人、北京2人、湖北1人、湖南1人、广东1人、贵州1人,其中年龄最大的是我,50岁。年龄最小的是王琳,22岁。
2003年7月15日早8点多,我们乘汽车从喀什出发前往慕士塔格。先是经过一片远处能望见雪山的平坦地带,然后进入了两边都是崇山俊岭的河谷,这条河谷很长很长,汽车在里面开了好几个小时。穿过河谷,转到山背后,就离慕士塔格不远了。再往前开一点,到了卡拉库里湖边,车在那里停了一下,让大家去拍照。这里真是个极美的地方。高大的公格尔峰、公格尔九别峰、慕士塔格都在湖对面。兰净的天空,洁白的雪山,清澈的湖水,湖边绿茵茵的小草,交织在一起使人产生一种这里离天堂不远的感觉。让人在感叹美的同时又对大自然怀有几分敬意。
没多久,宋玉江就喊大家快走,说时间不够了,再耽搁天黑之前就到不了大本营了。车又往前开了20分钟,大约下午5点半,停在了一个叫苏巴什的小村旁。我们从汽车上卸下所有物资,当地村民再把这些物品捆到骆驼背上。这里海拔3600米,离海拔4350米的登山大本营还有8公里。
留下杨春风和两个高山协作跟着还没装完的驼队,其他人就都于6点半左右空着手先走了。刚开始大家都在一起走,但我不习惯于慢走,没走多远就不耐烦了。问了问大致该怎么走后就以自己的速度在前边猛走了。
到了大本营的位置,见那里约有40多顶帐篷。中国科学院冰川考察队住的是几座营房式的大帐篷,其他基本上都是小帐篷。最多的是来自国外的登山和滑雪爱好者。当时国内的只有北京的杨立群、刘雪鹏各带一支队伍已在山上。此外还有来此挣钱的附近村民搭起的一些帐篷,附近居住的都是克尔克孜族人。我到那里已经是9点15分了(北京时间,那里和北京时差约3小时),太阳就要落山了,我却只穿着短袖上衣和短裤。百十米外就是冰川,我开始觉得有点冷,但衣服都在骆驼背上,驼队还没到。不久太阳落山了,我就更冷了。后来,驼队陆续到了,但领队还没到,没有确定扎营地点还不能把驼背上的东西放下来。等了一个小时,终于从驼背上取下了大背包,穿上了长衣长裤。幸亏我已练了6年冬泳,要不然非冻出病来不可。当晚搭完帐篷,简单吃点东西,已是夜里1点了。
16日休息,吃过早饭,不知不觉营地周围站满了附近的村民,好象随时都会涌过来抢我们东西似的,看起来怪可怕的。其实他们都很淳朴,只想找点挣钱的机会。只要你的东西放在帐篷内,不管营地有人没人都不会丢失。营地旁有一条小河,是山上冰雪溶化流下来的水。很凉,也很混浊,早晨上面还会冻上一层薄冰。我们的一切用水都取自这小河。白天没事坐在营地旁看着山上往来的人影觉得很好玩,看人家在山上滑雪更是羡慕。
17日开始适应性练习,目标是1号营地,英文叫Campl,简称C1。到C1后再返回大本营,同时也往C1运送一些物品。刚上山坡时路还好走一点,后来就是在碎石堆上走,一边走一边往下滑,搅动的尘土还直冒烟,呛得嗓子难受。越走越累,越走越慢。4800米以上开始有积雪。再往上走一段就开始有散布在雪坡上的帐篷。我们的营地比别人的都高,位置在5580米处。营地上面是嵯峨的雪峰,下面是一处较陡的雪坡,虽然只有几十米高,但积雪很厚,走起来比较费力。比我先到的几个人停在雪坡下休息,我听说上去就到了,就一鼓作气地冲了上去。
下山时遇见落在后面的队友有些都累得快支持不住了。尤其一个女队友,到了一号营地最低一座帐篷处(离我们营地高差约500米)就退了回去。不但走的奇慢,还走几步就要呕吐一遍。我这里绝无贬意,后来这位队友也登顶了。我只想说明有严重高山反应的人也能登顶,鼓励后来人不要泄气。大个和我本想照顾她下山,可是她太慢了,最后我们终于忍不住先走了。反正后面还有那么多人,也不乏爱美之徒。
根据这次到达C1的先后,领队把大家分成两组,第一组6人,基本上都是先到达的,是尽可能保证登顶的。另外7人被分在第二组。我自然在第一组内。
18日休息一天,19日第一组上C1,计划在那里住一晚上,第二天上C2后再返回大本营。那天晚上到C1后大家都懒得动,除了宋玉江外大家也不太会用汽油炉。大个给我一袋自热食品,此外就喝了点热水。第二天早晨竟没吃饭,出发又晚。一开始就是较陡的大雪坡。我第一次穿高山靴,很不习惯。上了第一个坡后,宋玉江帮我绑上了踏雪板。这下子更完了,本来高山靴就非常笨重,踏雪板又比鞋底宽出许多,一迈步是不这脚踩那脚,就是那脚踩这脚,简直象刚学走路的小孩,不知该怎么迈步了。上坡、下坡、再上坡,勉强走到离雪桥不远的地方,还不到计划行程的一半,又饿得头昏眼花。我就不再往前走,自己退了回来。其他队友有些吃了自带的能量棒,没穿踏雪板而用自带的冰爪。个别人虽然也没吃东西,也用踏要板,但没我那么笨,所以情况都比我好。不过由于时间关系也都没到C2就退回来了。后来的情况证明:冰爪在C1到C2的这段路上,在上午雪比较硬的情况下才有些优势,在比较松软的雪上,还是要穿踏雪板。
这次下山要休息两天,我们都鼓动宋玉江要到离大本营约100公里的塔什库尔干去玩一趟。宋玉江通过电台和在C2的杨春风商议后同意了这个要求,因为大本营食品不足了,也正需要补充。
21日吃过早饭,我们7个人开始向公路方向走去。在山坡上可以看见公路离大本营的最近点,我就直接朝着那一点走。转过几个小山坡,见其他人都没跟过来,也见不到他们的人影,我想他们可能愿意沿着路走,不肯抄近,反正最后都要到那个地方,我就自己走吧。反复上坡下坡又过河,1个多小时后我走到了公路旁,在那里等其他队友,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看山下他们应该经过的那片平地上连个人影都没有。我一想,坏了,他们准是从路上经过的一个小村庄租车跑了,那村子里有一个被称作江别克的年轻人有辆吉普车。可事先也没说要从那里租车呀?我怎么办?回去又很不甘心,错过这次机会,可能今生再也不会到塔什库尔干了。狠了狠心,还是要去。于是开始拦车。这条路上本来车就少,而那些车又都不肯停,也可能因为我身材高大又不象个好人吧。我就沿公路往前走,打算一边走一边拦车,我就不信一天拦不到一辆车。当走到最高的山口处仰望慕士塔格时,见慕峰就象一个裂成了几瓣的开花馒头。虽然当天属于多云间晴的天气,但慕峰顶上却笼罩着浓密的乌云。这一天是杨立群他们计划登顶的日子,我心想,完了,杨立群他们可能登不了顶了,心里也怪难受的。
沿着公路走了5公里的时候,后面又来了一辆集装箱大卡车。我没抱什么希望地向这辆车招了招手,没想到这辆车还真停下来了。再往驾驶室里一看,原来里边坐着我的3个队友,我太高兴了!上车后听他们说,他们只租车从那个小村子开到公路边,然后拦了这辆车把他们带过来,另3个人在后面的一辆车上。
塔什库尔干的县城没有多大,也没有什么高大建筑,有几条街道还是土马路,但却有着浓郁的异域风情。这里主要居住着塔吉克族人,人们多穿着色彩鲜艳的民族服装,讲着本民族的语言,连大街上的警察也是白皮肤、高鼻梁、兰眼睛。
到了这里,找好住处后大家最强烈的欲望就是要大吃一顿。虽然在大本营我们登山队的伙食比起其他登山队来要好,但比起山下来还是艰苦多了。我们找了一家小饭馆,让他们把桌子摆在屋子外面,要了很多有营养的菜,然后就贪婪地吃起来。可谁知要把这些美味佳肴吃下去竟成了一件很痛苦的事。大家在山上被强烈的紫外线照得皮肤黝黑还不说,嘴上还满是深深的裂纹。尽管抹了防晒霜,尽管时常喝水,还是阻止不了大自然要给你点颜色看。尤其是大个,可能是防晒霜质量有问题使皮肤过敏,满脸都是皱褶,活象一只大猩猩。当辣辣的菜肴接触到嘴上的裂纹时,大家都疼得呲牙咧嘴。
我们吃饭的时候,有一个自称是武汉人名叫詹蓓妮的年轻漂亮姑娘,走过来和我们搭话,说她是只身来新疆旅游的,明天打算到红其拉甫山口去,并询问我们的情况。大家见到漂亮女人都来了兴致,对她说那个山口没什么意思,还是跟我们到慕土塔格去吧。个别人更是殷勤有加,小詹好象终于被说服了,决定第二天搭我们的车到大本营去看看登山是什么样子。
22日一早起来觉得浑身酸疼,我以为是头一天在4000米左右的山上走了10多公里累的,后来知道别人也都有同样的感觉,说是因为洗热水澡洗的。我真担心这会影响后面的登山。
起来后我一个人出去转转,先到了城边的金草滩。那里是河湾边的一大片高原湿地,上面长满了鲜绿的野草。草滩上有许多牛羊和人,还有在进行训练的武警战士。草滩中还分布着许多浅水坑,有些地方一踩上去就往下陷。看完了金草滩又去看紧挨着草滩的唐代古城遗址。遗址不算很小,在一个不高的山头上,周围是古城墙的残垣,中间是曾经建造过房屋的一堆堆乱石和土块。确实能给人一种震撼的沧桑感。
吃过早饭,宋玉江找来一辆小卡车,然后买了些粮食,肉类和西瓜、哈密瓜等。小詹也按时赶来,我们乘车返回了大本营。到了营地,那些男队友们见了小詹眼睛都直闪光。
到了傍晚,见一队人背着大包从山上下来,估计是杨立群他们。我迎上去看望,果然他们因天气恶劣没能登顶。我心情沉重地说了几句安慰话,又回我们的营地抱一个西瓜给他们送过去。
当天晚上,杨春风把自己的帐蓬让给小詹一个人住,当得知第二天早晨冰川考察队有人下山,就决定让小詹随冰川队的人一起离开,小詹还没呆够,但也只好不情愿地走了,有些男队友们更是恋恋不舍,还带着深深的遗憾。
23日再上C1,在C1住了一夜,24日上C2,这次要在6350米的C2住一晚上。那天我走得比较拼命,所以只有穿冰爪的老狗超过了我。但到了营地后觉得很累,只想睡觉。结果白天睡了,晚上却睡不好了。不过还行,不算严重。25日我们从C2回大本营,第二组从C1上C2。
26日、27日休息,这次再看到山上往来的人影就不再觉得好玩了,因为知道了登顶并不容易,甚至怀疑自己到底该不该来。我常常躺在一块大石头上睡觉,其他人多数都聚在一起聊天,讲的主要是一些黄色语言,每天都这样。当然这并不能说明他们品行有问题。事后我开玩笑说,我本以为登高山是件很神圣的事情,没想到流氓也爱登山。
那几天有三个从西安来登慕峰的,上到C1因炉子不好使退了回来,把帐篷就搭在我们营地边上,并且也和我们一起吃饭。他们打算和我们一起上山,我们怕受拖累,影响我们登顶,就坚决反对。有些队员甚至背后说他们要跟着走就把他们打回去。其实何必呢,各走各的,各不负责不就完了吗。可一些人说如果他们出了问题我们不救援以后在登山界会名声很臭的。后来3人中有1人不上山了,另两个在27日就上了C1。我们到C1时他们在帐篷里没露面,我们上C2时也没见他们在后面跟着。据说他们在我们后面走,还没到C2就因体力不支退回去了。也难怪,他们背的东西比我们要重得多。
28日下午,在我们第一组出发前全队所有人员在一起合了影,然后就在有些悲壮的气氛中出发了,这次是杨春风和我们一起走。我和老狗走在最前面,在离C1还有一半的路程上遇见了成功登顶后下山的刘雪鹏,向他们表示祝贺后大家又一起聊了几句。尽管登山圈里对刘雪鹏有些非议。但我还是很佩服他的。
又往上走了一段,天空中飘起了雪花,我们知道,季节到了,天气要转冷了。这次在C1,两个高山协作都和我们在一起,有他们为我们做晚饭吃情况就好多了。29日开始往C2走。因为前几天气温较高,低处的雪有些溶化,C1附近变成了半冰半雪的状态,帐篷旁和雪坡上都出现了许多冰裂缝,但是不宽,不至于把人掉下去。上第一个大雪坡时要非常小心,要不然容易滑下去。
这次我总结了前几次的经验就有意慢走,以免累过分了不好恢复。我知道前一阶段我已经吃了两次亏,一是刚到大本营时冻了1个多小时,虽然没有病倒,也是连续几天都不舒服。二是去塔什库尔干的路上行走太多,不易恢复。总之一句话,就是太狂了,使自己受到了损害,狂妄对于登高山真是有害无益呀。这次知道反正时间来得及。慢走本身也是个适应的过程,还可以多保存些体能。不过话又说回来,就是想快走也快不了多少,每走十几步都要停下来喘一阵气,等气喘匀了再走。喘气时拄着登山杖,闭着眼睛,连眼皮抬起来都觉得累。从C1到C2,从C2到C3,我差不多都是最后一个到的。杨春风多次担心地问我:“老张,行吗?”,我说没事。
我们到C2,普布和旺青去建C3了。没有他们给我们做饭,我们又胡乱吃点就算了。我只吃了一点方便面稀汤。到了高海拔的地方,不光人有高山反应,就连食品也有高山反应。巧克力、奶酪、牛肉干都变得邦邦硬,难以咀嚼,也不好吃。
C1设三顶帐篷,C2和C3各设两顶帐篷。因为我是最后到C2的,我到时他们已经每三个人进了一顶帐篷,我的睡袋和防潮垫在深圳三个队友的帐篷里。他们不愿让我进去,我让他们把我的东西找出来,然后就跑到冰川队的帐篷里去了。他们的营地就在我们下面几米远的地方,那几天没人,帐篷里空着,我一个人睡更舒服。
30日到C3,C3在6950米,那里就没有冰川队的营地了。加上普布和旺青,9个人挤在两顶帐篷里自然是不好休息。夜里我觉得有些胃疼,但大家都没带治胃病的药,就只好忍着了。
31日,因为要登顶了,天还没亮大家就起来了,我求普布帮我绑上了踏雪板,因为本来就呼吸困难,再把身子弯成一团去捆那玩艺更是累人。大约早晨8点(相当于北京5点),我们离开C3前往顶峰。这天我的状态特别好,也可能是前两天有意慢走的结果吧。但一开始我并不知道,走了一阵就不自觉地超过了一个个队友走到了前面,但离杨春风还有几十步的距离。
天渐渐地亮了,身边的雾却越来越浓,能见度只有十几米。走着走着,杨春风突然转身退了回来,到我身边停下说:“咱们撤吧!”我说:“不能轻易放弃。”他说:“那周围哪都看不清怎么办?”我说“看不清就哪高往哪走。”后来他和大本营的电台联系,大本营说山上就一小片云。杨春风又接着往前走,我紧跟在后面。但走了一段踏雪板掉了,我自己不想弄,还想等普布来帮我,就坐在雪地上不走了。等过去了好几个人也没见普布上来,我只好自己把它捆上了。
穿过了云雾层,上面又刮起了大风,把山上的雪刮起来还是象大雾一样。看不见前面的人影,就连刚走过的脚印也立刻被大风抹平了。我重新超过了几个人,只是没追上老狗。我和老狗基本上是全队最快的两个。中午12点,终于到了山顶。杨春风一个人站在那里,我见东面和南面各有一条乱石堆,就问杨哪个高,杨说东面的那个高,我又顶着大风弯着腰到东面的乱石堆上走了走。周围都是雪雾,也看不清什么风景。但我想好不容易上来了,怎么也要在山顶上多呆一会,就坐在了雪地上。杨春风冷得受不了啦,让我在这等其他人,他先下去了。隔一会,先是吴小岚,然后是大个,再后就是甲荃,都陆续上来了。甲荃上来后高喊一声登顶了,我才从木然的心态下突然有所心动,和他拥抱了一下,眼里流出了激动的泪水。我让他为我拍照,但我的1700元的小傻瓜机失灵了,只好让他用他的相机为我照了一张。后来我又给他照,怕羽绒服的帽子挡相机镜头,就把帽子撩到了脑后。只这一会,下山后我的耳朵就掉了一层皮。
照完相他们相继下山了。因为海军还没上来,我继续在山上等,等了一会,也不知海军到底还上不上来了?我也下山了。走一段遇见普布陪着海军正往上走,在和他们打招呼的时候,大风吹得我原地转了360°。下山后海军经常提这个动作,说象跳交谊舞似的,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一个人向下走了一阵,意识到方向走偏了,有些偏左了,就一边向下走一边向右靠,最后又偏回了C3。在那里我卸下踏雪板捆到包上,打算顺着雪坡向下滑。谁知坡度不够,只能两手扒雪向下挪动,挪动一会手累了又站起来走。雪很深,没有踏雪板走起来费劲多了。走一段再往下滑,滑累了又走。现在想起来挺可笑的,踏雪板就在身上背着,可就是懒得重新装上。
到了C2,我又往包里装了二组的一个睡袋和一个防潮垫。因为我们自己的放在C3没往回背,这样二组就不用再往上背这些东西了。可以减轻点重量,我们的东西再由二组背下来。我觉得这样也未必好,因为人较杂,素质不一定都高,万一有什么差错也不好解决。
在C2,又遇见了另一个国内的登山队,队员有四川的、陕西的和新疆的。他们在这里没自建营地,就住在冰川队的帐篷里。他们的登顶日期是8月2日,可那天我们在大本营看山上天气不怎么好,认为他们登不了顶了。后来听说也都登顶了。这是可能的,因为在大本营看不到山顶,只能看到相当于C2的高度,可能那天的云只在半山腰,C3以上还是晴的。这种现象也是不少见的。
本来计划在C2住一晚上再下山,但是都知道这里没什么好吃的,睡也不舒服,所心就下决心干脆当天回到大本营去。从C2往下走一段后觉得有些恶心,后来就忍不住吐了。其实肚子里没什么东西,只是往外吐又酸又苦的水。这是我到慕峰17天以来首次恶心呕吐。
下到C1,休息一会,从帐篷里翻出点糖果吃,换下羽绒服和高山靴又往下走。75升的大背包已经装满,高山靴没处放,只好挂在脖子上,没多久就勒得我脖子疼。中途遇见拉着毛驴上山的几个村民,真想把东西放到驴背上去 ,但他们要价太高,我无法接受,只好忍着饥饿和疲劳继续背着沉重的大包向下走。晚上11点半,我第一个回到了大本营,比其他队友早了1个小时。
在大本营,有冰川站的人过来说我们有人在C1上面的雪坡上滑坠了,滚到悬崖下面去了,说他们是从望远镜里看到的,等人到齐了才知道,是大个带的防潮垫滚下去了。当晚杨春风留在C2预备接应。普布和旺青继续在C3协助二组登顶。
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饭后觉得胃不舒服,接着把吃的东西全吐出来了。当时大本营已经没有什么可口的东西了。中午、晚上我都没吃饭,胃疼,经常呕吐。后来传来消息,二组也全部登顶了。
8月2日,老宋给我做点玉米面糊,总算有点能咽下去的东西,但还是胃疼,时常呕吐。这天,老周、八戒、王琳较早地返回了大本营。然后老周和八戒也去了塔什库尔干,打算从那里直接回喀什。二组的其他人也陆续返回了大本营。吃过晚饭,大家开始认找自己的睡袋和防潮垫,可我的睡袋找不到了,那是Camp牌1100克鹅绒的,据说相当于1500克的鸭绒睡袋。我和宋玉江说了这事,当时天也黑了,宋说明天再找吧。第二天早晨我又各处找了一遍,只是没到各人的帐篷里去找,还是没找到。吃早饭时我又和宋说,宋说吃完饭和我一起去找。又找时见我的睡袋被扔在外面,但没有了压缩袋。宋给我找了一个没有压缩功能的袋子套上,也不便再去翻每个人的东西了。
本来计划3日撤营下山的,但因事先没联系好骆驼,下山又推迟了一天。大个和深圳的三个队友着急回去,甘脆背上自己的东西走到公路边拦车走了。领队本想让我和他们一起走,以防病情恶化发生意外,但因我胃疼得厉害,无法收拾东西而没走成。少了6个人,我们的营地冷清了许多,天气也更冷了。
8月4日,阴天,还飘着雪花。大家吃完早饭后就开始撤营。来的时候我是最能干的,可临走时我的身体已非常虚弱,什么也不能干了,连我自己的东西还是普布帮忙收拾的呢。大家还没忙完的时候,领队就让我和芳芳骑着毛驴先下山了。不然我是真走不下去了。想想来时和走时的鲜明对比,心里还真有点不是滋味。整个登山过程中都很英勇的我,没想到下山后翻了船。
紧贴着地面的一簇簇紫红色小花有些蔫了,好象为和我们分别而难过。几只土拔鼠象人似的站在不远处注视着我们,好象在为我们送行。渐渐地离开慕士塔格,骑在驴背上,不时地回首望望那雄伟圣洁的山体,心里有一种平静的满足。在我看来,每一座高山都是神圣的,我不光是来登山,也是来朝圣的。登顶的成功也就是圆满地完成了一次朝圣活动。尽管我是带着病痛和极度虚弱的身体离开的,但无论什么也改变不了我对高山的痴情。如果将来有条件,我还要到更高的山峰去朝圣。
写于2004年3月17日~21日
我第一次登雪山就选择了海拨7546米的慕士塔格,而且居然成功地登顶了,全队13名队员都登顶了。不要因此就认为慕士塔格是一座多么容易攀登的山峰。从图片上看,慕士塔格是一条平缓的渐开线形状的大雪坡,其实那只是视觉效果,是山体的外轮廓线,在这条外轮廓线下还隐藏着许多复盖着厚厚积雪的沟谷和较陡的雪坡,尽管这里不需要什么攀登技术,但也很少有人认为登顶是轻松的。我们能成功也是多种因素的合成结果。首先是今年天气好,从我们7月15日到达大本营到8月4日离开大本营总共21天,山上没几天坏天气,据说往年可不是这样,而且山上的雪要比今年厚得多。其次我们参加的是乌鲁木齐市登山协会组织的商业登山活动。我们这样选择,就是为了用金钱来换取高成功率。参加商业登山活动的费用要比自助登山高得多,除了可以挥金如土的人,谁能不仔细审视一下自己的实力再作决定呢?比如说我吧,那也是因为以前曾到过珠穆朗玛峰5800米处没有任何高山反应才大着胆子下这个决心的。其他多数人都有过多次登雪山的经历。
我们这支队伍共有18人。领队杨春风,副领队宋玉江,大本营总管兼厨师1人,还从西藏登山学校请来高山协作2人,普布顿珠和索玛旺青。13名队员中四川4人、深圳3人、北京2人、湖北1人、湖南1人、广东1人、贵州1人,其中年龄最大的是我,50岁。年龄最小的是王琳,22岁。
2003年7月15日早8点多,我们乘汽车从喀什出发前往慕士塔格。先是经过一片远处能望见雪山的平坦地带,然后进入了两边都是崇山俊岭的河谷,这条河谷很长很长,汽车在里面开了好几个小时。穿过河谷,转到山背后,就离慕士塔格不远了。再往前开一点,到了卡拉库里湖边,车在那里停了一下,让大家去拍照。这里真是个极美的地方。高大的公格尔峰、公格尔九别峰、慕士塔格都在湖对面。兰净的天空,洁白的雪山,清澈的湖水,湖边绿茵茵的小草,交织在一起使人产生一种这里离天堂不远的感觉。让人在感叹美的同时又对大自然怀有几分敬意。
没多久,宋玉江就喊大家快走,说时间不够了,再耽搁天黑之前就到不了大本营了。车又往前开了20分钟,大约下午5点半,停在了一个叫苏巴什的小村旁。我们从汽车上卸下所有物资,当地村民再把这些物品捆到骆驼背上。这里海拔3600米,离海拔4350米的登山大本营还有8公里。
留下杨春风和两个高山协作跟着还没装完的驼队,其他人就都于6点半左右空着手先走了。刚开始大家都在一起走,但我不习惯于慢走,没走多远就不耐烦了。问了问大致该怎么走后就以自己的速度在前边猛走了。
到了大本营的位置,见那里约有40多顶帐篷。中国科学院冰川考察队住的是几座营房式的大帐篷,其他基本上都是小帐篷。最多的是来自国外的登山和滑雪爱好者。当时国内的只有北京的杨立群、刘雪鹏各带一支队伍已在山上。此外还有来此挣钱的附近村民搭起的一些帐篷,附近居住的都是克尔克孜族人。我到那里已经是9点15分了(北京时间,那里和北京时差约3小时),太阳就要落山了,我却只穿着短袖上衣和短裤。百十米外就是冰川,我开始觉得有点冷,但衣服都在骆驼背上,驼队还没到。不久太阳落山了,我就更冷了。后来,驼队陆续到了,但领队还没到,没有确定扎营地点还不能把驼背上的东西放下来。等了一个小时,终于从驼背上取下了大背包,穿上了长衣长裤。幸亏我已练了6年冬泳,要不然非冻出病来不可。当晚搭完帐篷,简单吃点东西,已是夜里1点了。
16日休息,吃过早饭,不知不觉营地周围站满了附近的村民,好象随时都会涌过来抢我们东西似的,看起来怪可怕的。其实他们都很淳朴,只想找点挣钱的机会。只要你的东西放在帐篷内,不管营地有人没人都不会丢失。营地旁有一条小河,是山上冰雪溶化流下来的水。很凉,也很混浊,早晨上面还会冻上一层薄冰。我们的一切用水都取自这小河。白天没事坐在营地旁看着山上往来的人影觉得很好玩,看人家在山上滑雪更是羡慕。
17日开始适应性练习,目标是1号营地,英文叫Campl,简称C1。到C1后再返回大本营,同时也往C1运送一些物品。刚上山坡时路还好走一点,后来就是在碎石堆上走,一边走一边往下滑,搅动的尘土还直冒烟,呛得嗓子难受。越走越累,越走越慢。4800米以上开始有积雪。再往上走一段就开始有散布在雪坡上的帐篷。我们的营地比别人的都高,位置在5580米处。营地上面是嵯峨的雪峰,下面是一处较陡的雪坡,虽然只有几十米高,但积雪很厚,走起来比较费力。比我先到的几个人停在雪坡下休息,我听说上去就到了,就一鼓作气地冲了上去。
下山时遇见落在后面的队友有些都累得快支持不住了。尤其一个女队友,到了一号营地最低一座帐篷处(离我们营地高差约500米)就退了回去。不但走的奇慢,还走几步就要呕吐一遍。我这里绝无贬意,后来这位队友也登顶了。我只想说明有严重高山反应的人也能登顶,鼓励后来人不要泄气。大个和我本想照顾她下山,可是她太慢了,最后我们终于忍不住先走了。反正后面还有那么多人,也不乏爱美之徒。
根据这次到达C1的先后,领队把大家分成两组,第一组6人,基本上都是先到达的,是尽可能保证登顶的。另外7人被分在第二组。我自然在第一组内。
18日休息一天,19日第一组上C1,计划在那里住一晚上,第二天上C2后再返回大本营。那天晚上到C1后大家都懒得动,除了宋玉江外大家也不太会用汽油炉。大个给我一袋自热食品,此外就喝了点热水。第二天早晨竟没吃饭,出发又晚。一开始就是较陡的大雪坡。我第一次穿高山靴,很不习惯。上了第一个坡后,宋玉江帮我绑上了踏雪板。这下子更完了,本来高山靴就非常笨重,踏雪板又比鞋底宽出许多,一迈步是不这脚踩那脚,就是那脚踩这脚,简直象刚学走路的小孩,不知该怎么迈步了。上坡、下坡、再上坡,勉强走到离雪桥不远的地方,还不到计划行程的一半,又饿得头昏眼花。我就不再往前走,自己退了回来。其他队友有些吃了自带的能量棒,没穿踏雪板而用自带的冰爪。个别人虽然也没吃东西,也用踏要板,但没我那么笨,所以情况都比我好。不过由于时间关系也都没到C2就退回来了。后来的情况证明:冰爪在C1到C2的这段路上,在上午雪比较硬的情况下才有些优势,在比较松软的雪上,还是要穿踏雪板。
这次下山要休息两天,我们都鼓动宋玉江要到离大本营约100公里的塔什库尔干去玩一趟。宋玉江通过电台和在C2的杨春风商议后同意了这个要求,因为大本营食品不足了,也正需要补充。
21日吃过早饭,我们7个人开始向公路方向走去。在山坡上可以看见公路离大本营的最近点,我就直接朝着那一点走。转过几个小山坡,见其他人都没跟过来,也见不到他们的人影,我想他们可能愿意沿着路走,不肯抄近,反正最后都要到那个地方,我就自己走吧。反复上坡下坡又过河,1个多小时后我走到了公路旁,在那里等其他队友,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看山下他们应该经过的那片平地上连个人影都没有。我一想,坏了,他们准是从路上经过的一个小村庄租车跑了,那村子里有一个被称作江别克的年轻人有辆吉普车。可事先也没说要从那里租车呀?我怎么办?回去又很不甘心,错过这次机会,可能今生再也不会到塔什库尔干了。狠了狠心,还是要去。于是开始拦车。这条路上本来车就少,而那些车又都不肯停,也可能因为我身材高大又不象个好人吧。我就沿公路往前走,打算一边走一边拦车,我就不信一天拦不到一辆车。当走到最高的山口处仰望慕士塔格时,见慕峰就象一个裂成了几瓣的开花馒头。虽然当天属于多云间晴的天气,但慕峰顶上却笼罩着浓密的乌云。这一天是杨立群他们计划登顶的日子,我心想,完了,杨立群他们可能登不了顶了,心里也怪难受的。
沿着公路走了5公里的时候,后面又来了一辆集装箱大卡车。我没抱什么希望地向这辆车招了招手,没想到这辆车还真停下来了。再往驾驶室里一看,原来里边坐着我的3个队友,我太高兴了!上车后听他们说,他们只租车从那个小村子开到公路边,然后拦了这辆车把他们带过来,另3个人在后面的一辆车上。
塔什库尔干的县城没有多大,也没有什么高大建筑,有几条街道还是土马路,但却有着浓郁的异域风情。这里主要居住着塔吉克族人,人们多穿着色彩鲜艳的民族服装,讲着本民族的语言,连大街上的警察也是白皮肤、高鼻梁、兰眼睛。
到了这里,找好住处后大家最强烈的欲望就是要大吃一顿。虽然在大本营我们登山队的伙食比起其他登山队来要好,但比起山下来还是艰苦多了。我们找了一家小饭馆,让他们把桌子摆在屋子外面,要了很多有营养的菜,然后就贪婪地吃起来。可谁知要把这些美味佳肴吃下去竟成了一件很痛苦的事。大家在山上被强烈的紫外线照得皮肤黝黑还不说,嘴上还满是深深的裂纹。尽管抹了防晒霜,尽管时常喝水,还是阻止不了大自然要给你点颜色看。尤其是大个,可能是防晒霜质量有问题使皮肤过敏,满脸都是皱褶,活象一只大猩猩。当辣辣的菜肴接触到嘴上的裂纹时,大家都疼得呲牙咧嘴。
我们吃饭的时候,有一个自称是武汉人名叫詹蓓妮的年轻漂亮姑娘,走过来和我们搭话,说她是只身来新疆旅游的,明天打算到红其拉甫山口去,并询问我们的情况。大家见到漂亮女人都来了兴致,对她说那个山口没什么意思,还是跟我们到慕土塔格去吧。个别人更是殷勤有加,小詹好象终于被说服了,决定第二天搭我们的车到大本营去看看登山是什么样子。
22日一早起来觉得浑身酸疼,我以为是头一天在4000米左右的山上走了10多公里累的,后来知道别人也都有同样的感觉,说是因为洗热水澡洗的。我真担心这会影响后面的登山。
起来后我一个人出去转转,先到了城边的金草滩。那里是河湾边的一大片高原湿地,上面长满了鲜绿的野草。草滩上有许多牛羊和人,还有在进行训练的武警战士。草滩中还分布着许多浅水坑,有些地方一踩上去就往下陷。看完了金草滩又去看紧挨着草滩的唐代古城遗址。遗址不算很小,在一个不高的山头上,周围是古城墙的残垣,中间是曾经建造过房屋的一堆堆乱石和土块。确实能给人一种震撼的沧桑感。
吃过早饭,宋玉江找来一辆小卡车,然后买了些粮食,肉类和西瓜、哈密瓜等。小詹也按时赶来,我们乘车返回了大本营。到了营地,那些男队友们见了小詹眼睛都直闪光。
到了傍晚,见一队人背着大包从山上下来,估计是杨立群他们。我迎上去看望,果然他们因天气恶劣没能登顶。我心情沉重地说了几句安慰话,又回我们的营地抱一个西瓜给他们送过去。
当天晚上,杨春风把自己的帐蓬让给小詹一个人住,当得知第二天早晨冰川考察队有人下山,就决定让小詹随冰川队的人一起离开,小詹还没呆够,但也只好不情愿地走了,有些男队友们更是恋恋不舍,还带着深深的遗憾。
23日再上C1,在C1住了一夜,24日上C2,这次要在6350米的C2住一晚上。那天我走得比较拼命,所以只有穿冰爪的老狗超过了我。但到了营地后觉得很累,只想睡觉。结果白天睡了,晚上却睡不好了。不过还行,不算严重。25日我们从C2回大本营,第二组从C1上C2。
26日、27日休息,这次再看到山上往来的人影就不再觉得好玩了,因为知道了登顶并不容易,甚至怀疑自己到底该不该来。我常常躺在一块大石头上睡觉,其他人多数都聚在一起聊天,讲的主要是一些黄色语言,每天都这样。当然这并不能说明他们品行有问题。事后我开玩笑说,我本以为登高山是件很神圣的事情,没想到流氓也爱登山。
那几天有三个从西安来登慕峰的,上到C1因炉子不好使退了回来,把帐篷就搭在我们营地边上,并且也和我们一起吃饭。他们打算和我们一起上山,我们怕受拖累,影响我们登顶,就坚决反对。有些队员甚至背后说他们要跟着走就把他们打回去。其实何必呢,各走各的,各不负责不就完了吗。可一些人说如果他们出了问题我们不救援以后在登山界会名声很臭的。后来3人中有1人不上山了,另两个在27日就上了C1。我们到C1时他们在帐篷里没露面,我们上C2时也没见他们在后面跟着。据说他们在我们后面走,还没到C2就因体力不支退回去了。也难怪,他们背的东西比我们要重得多。
28日下午,在我们第一组出发前全队所有人员在一起合了影,然后就在有些悲壮的气氛中出发了,这次是杨春风和我们一起走。我和老狗走在最前面,在离C1还有一半的路程上遇见了成功登顶后下山的刘雪鹏,向他们表示祝贺后大家又一起聊了几句。尽管登山圈里对刘雪鹏有些非议。但我还是很佩服他的。
又往上走了一段,天空中飘起了雪花,我们知道,季节到了,天气要转冷了。这次在C1,两个高山协作都和我们在一起,有他们为我们做晚饭吃情况就好多了。29日开始往C2走。因为前几天气温较高,低处的雪有些溶化,C1附近变成了半冰半雪的状态,帐篷旁和雪坡上都出现了许多冰裂缝,但是不宽,不至于把人掉下去。上第一个大雪坡时要非常小心,要不然容易滑下去。
这次我总结了前几次的经验就有意慢走,以免累过分了不好恢复。我知道前一阶段我已经吃了两次亏,一是刚到大本营时冻了1个多小时,虽然没有病倒,也是连续几天都不舒服。二是去塔什库尔干的路上行走太多,不易恢复。总之一句话,就是太狂了,使自己受到了损害,狂妄对于登高山真是有害无益呀。这次知道反正时间来得及。慢走本身也是个适应的过程,还可以多保存些体能。不过话又说回来,就是想快走也快不了多少,每走十几步都要停下来喘一阵气,等气喘匀了再走。喘气时拄着登山杖,闭着眼睛,连眼皮抬起来都觉得累。从C1到C2,从C2到C3,我差不多都是最后一个到的。杨春风多次担心地问我:“老张,行吗?”,我说没事。
我们到C2,普布和旺青去建C3了。没有他们给我们做饭,我们又胡乱吃点就算了。我只吃了一点方便面稀汤。到了高海拔的地方,不光人有高山反应,就连食品也有高山反应。巧克力、奶酪、牛肉干都变得邦邦硬,难以咀嚼,也不好吃。
C1设三顶帐篷,C2和C3各设两顶帐篷。因为我是最后到C2的,我到时他们已经每三个人进了一顶帐篷,我的睡袋和防潮垫在深圳三个队友的帐篷里。他们不愿让我进去,我让他们把我的东西找出来,然后就跑到冰川队的帐篷里去了。他们的营地就在我们下面几米远的地方,那几天没人,帐篷里空着,我一个人睡更舒服。
30日到C3,C3在6950米,那里就没有冰川队的营地了。加上普布和旺青,9个人挤在两顶帐篷里自然是不好休息。夜里我觉得有些胃疼,但大家都没带治胃病的药,就只好忍着了。
31日,因为要登顶了,天还没亮大家就起来了,我求普布帮我绑上了踏雪板,因为本来就呼吸困难,再把身子弯成一团去捆那玩艺更是累人。大约早晨8点(相当于北京5点),我们离开C3前往顶峰。这天我的状态特别好,也可能是前两天有意慢走的结果吧。但一开始我并不知道,走了一阵就不自觉地超过了一个个队友走到了前面,但离杨春风还有几十步的距离。
天渐渐地亮了,身边的雾却越来越浓,能见度只有十几米。走着走着,杨春风突然转身退了回来,到我身边停下说:“咱们撤吧!”我说:“不能轻易放弃。”他说:“那周围哪都看不清怎么办?”我说“看不清就哪高往哪走。”后来他和大本营的电台联系,大本营说山上就一小片云。杨春风又接着往前走,我紧跟在后面。但走了一段踏雪板掉了,我自己不想弄,还想等普布来帮我,就坐在雪地上不走了。等过去了好几个人也没见普布上来,我只好自己把它捆上了。
穿过了云雾层,上面又刮起了大风,把山上的雪刮起来还是象大雾一样。看不见前面的人影,就连刚走过的脚印也立刻被大风抹平了。我重新超过了几个人,只是没追上老狗。我和老狗基本上是全队最快的两个。中午12点,终于到了山顶。杨春风一个人站在那里,我见东面和南面各有一条乱石堆,就问杨哪个高,杨说东面的那个高,我又顶着大风弯着腰到东面的乱石堆上走了走。周围都是雪雾,也看不清什么风景。但我想好不容易上来了,怎么也要在山顶上多呆一会,就坐在了雪地上。杨春风冷得受不了啦,让我在这等其他人,他先下去了。隔一会,先是吴小岚,然后是大个,再后就是甲荃,都陆续上来了。甲荃上来后高喊一声登顶了,我才从木然的心态下突然有所心动,和他拥抱了一下,眼里流出了激动的泪水。我让他为我拍照,但我的1700元的小傻瓜机失灵了,只好让他用他的相机为我照了一张。后来我又给他照,怕羽绒服的帽子挡相机镜头,就把帽子撩到了脑后。只这一会,下山后我的耳朵就掉了一层皮。
照完相他们相继下山了。因为海军还没上来,我继续在山上等,等了一会,也不知海军到底还上不上来了?我也下山了。走一段遇见普布陪着海军正往上走,在和他们打招呼的时候,大风吹得我原地转了360°。下山后海军经常提这个动作,说象跳交谊舞似的,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一个人向下走了一阵,意识到方向走偏了,有些偏左了,就一边向下走一边向右靠,最后又偏回了C3。在那里我卸下踏雪板捆到包上,打算顺着雪坡向下滑。谁知坡度不够,只能两手扒雪向下挪动,挪动一会手累了又站起来走。雪很深,没有踏雪板走起来费劲多了。走一段再往下滑,滑累了又走。现在想起来挺可笑的,踏雪板就在身上背着,可就是懒得重新装上。
到了C2,我又往包里装了二组的一个睡袋和一个防潮垫。因为我们自己的放在C3没往回背,这样二组就不用再往上背这些东西了。可以减轻点重量,我们的东西再由二组背下来。我觉得这样也未必好,因为人较杂,素质不一定都高,万一有什么差错也不好解决。
在C2,又遇见了另一个国内的登山队,队员有四川的、陕西的和新疆的。他们在这里没自建营地,就住在冰川队的帐篷里。他们的登顶日期是8月2日,可那天我们在大本营看山上天气不怎么好,认为他们登不了顶了。后来听说也都登顶了。这是可能的,因为在大本营看不到山顶,只能看到相当于C2的高度,可能那天的云只在半山腰,C3以上还是晴的。这种现象也是不少见的。
本来计划在C2住一晚上再下山,但是都知道这里没什么好吃的,睡也不舒服,所心就下决心干脆当天回到大本营去。从C2往下走一段后觉得有些恶心,后来就忍不住吐了。其实肚子里没什么东西,只是往外吐又酸又苦的水。这是我到慕峰17天以来首次恶心呕吐。
下到C1,休息一会,从帐篷里翻出点糖果吃,换下羽绒服和高山靴又往下走。75升的大背包已经装满,高山靴没处放,只好挂在脖子上,没多久就勒得我脖子疼。中途遇见拉着毛驴上山的几个村民,真想把东西放到驴背上去 ,但他们要价太高,我无法接受,只好忍着饥饿和疲劳继续背着沉重的大包向下走。晚上11点半,我第一个回到了大本营,比其他队友早了1个小时。
在大本营,有冰川站的人过来说我们有人在C1上面的雪坡上滑坠了,滚到悬崖下面去了,说他们是从望远镜里看到的,等人到齐了才知道,是大个带的防潮垫滚下去了。当晚杨春风留在C2预备接应。普布和旺青继续在C3协助二组登顶。
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饭后觉得胃不舒服,接着把吃的东西全吐出来了。当时大本营已经没有什么可口的东西了。中午、晚上我都没吃饭,胃疼,经常呕吐。后来传来消息,二组也全部登顶了。
8月2日,老宋给我做点玉米面糊,总算有点能咽下去的东西,但还是胃疼,时常呕吐。这天,老周、八戒、王琳较早地返回了大本营。然后老周和八戒也去了塔什库尔干,打算从那里直接回喀什。二组的其他人也陆续返回了大本营。吃过晚饭,大家开始认找自己的睡袋和防潮垫,可我的睡袋找不到了,那是Camp牌1100克鹅绒的,据说相当于1500克的鸭绒睡袋。我和宋玉江说了这事,当时天也黑了,宋说明天再找吧。第二天早晨我又各处找了一遍,只是没到各人的帐篷里去找,还是没找到。吃早饭时我又和宋说,宋说吃完饭和我一起去找。又找时见我的睡袋被扔在外面,但没有了压缩袋。宋给我找了一个没有压缩功能的袋子套上,也不便再去翻每个人的东西了。
本来计划3日撤营下山的,但因事先没联系好骆驼,下山又推迟了一天。大个和深圳的三个队友着急回去,甘脆背上自己的东西走到公路边拦车走了。领队本想让我和他们一起走,以防病情恶化发生意外,但因我胃疼得厉害,无法收拾东西而没走成。少了6个人,我们的营地冷清了许多,天气也更冷了。
8月4日,阴天,还飘着雪花。大家吃完早饭后就开始撤营。来的时候我是最能干的,可临走时我的身体已非常虚弱,什么也不能干了,连我自己的东西还是普布帮忙收拾的呢。大家还没忙完的时候,领队就让我和芳芳骑着毛驴先下山了。不然我是真走不下去了。想想来时和走时的鲜明对比,心里还真有点不是滋味。整个登山过程中都很英勇的我,没想到下山后翻了船。
紧贴着地面的一簇簇紫红色小花有些蔫了,好象为和我们分别而难过。几只土拔鼠象人似的站在不远处注视着我们,好象在为我们送行。渐渐地离开慕士塔格,骑在驴背上,不时地回首望望那雄伟圣洁的山体,心里有一种平静的满足。在我看来,每一座高山都是神圣的,我不光是来登山,也是来朝圣的。登顶的成功也就是圆满地完成了一次朝圣活动。尽管我是带着病痛和极度虚弱的身体离开的,但无论什么也改变不了我对高山的痴情。如果将来有条件,我还要到更高的山峰去朝圣。
写于2004年3月17日~21日
 关于我们: CCT 康辉国旅- 四川中国康辉国际旅行社 『 点击查看电子地图 』
关于我们: CCT 康辉国旅- 四川中国康辉国际旅行社 『 点击查看电子地图 』CCT INTERNATIONAL TRAVEL SERVICE LTD
旅行社许可证号:L-SC-GJ00030 国际一类社
中国国家旅游局指定办理中国公民出入境游的国际旅行社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天仙桥北路3号SOHO大厦3楼 - 康辉国旅总部. 旅游接待A23室
TEL:86-28- 86082622 / 86082022 / 86080300 FAX: 86656234
Sponsored Links
特别声明:
A:关于美景旅游网独立原创文章图片等内容
1、美景旅游网原创文章、图片版权由我们全部保留;
2、美景旅游网原创文章、图片任何网站及媒体均可以免费使用,如转载我们的文章或图片,
请注明来自美景旅游网 并链接到 www.mjjq.com,商业用途请先联系我们;
3、免责:我们在我们能知悉的范围内努力保证所有采写文章的真实性和正确性,但不对真实性和正确性做任何保证。本站采写文章图片如果和事实有所出入,美景旅游网不承担连带责任;
B:关于美景旅游网采用非原创文章图片等内容
1、页面的文章、图片等等资料的版权归版权所有人所有。
2、免责:由于采集的图片、文章内容来源于互联网,内容页面标注的作者、出处和原版权者一致性无法确认,如果您是文章、图片等资料的版权所有人,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及时加上版权信息,如果您反对我们的使用,本着对版权人尊重的原则,我们会立即删除有版权问题的文章或图片内容。
3、本页面发表、转载的文章及图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A:关于美景旅游网独立原创文章图片等内容
1、美景旅游网原创文章、图片版权由我们全部保留;
2、美景旅游网原创文章、图片任何网站及媒体均可以免费使用,如转载我们的文章或图片,
请注明来自美景旅游网 并链接到 www.mjjq.com,商业用途请先联系我们;
3、免责:我们在我们能知悉的范围内努力保证所有采写文章的真实性和正确性,但不对真实性和正确性做任何保证。本站采写文章图片如果和事实有所出入,美景旅游网不承担连带责任;
B:关于美景旅游网采用非原创文章图片等内容
1、页面的文章、图片等等资料的版权归版权所有人所有。
2、免责:由于采集的图片、文章内容来源于互联网,内容页面标注的作者、出处和原版权者一致性无法确认,如果您是文章、图片等资料的版权所有人,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及时加上版权信息,如果您反对我们的使用,本着对版权人尊重的原则,我们会立即删除有版权问题的文章或图片内容。
3、本页面发表、转载的文章及图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西藏旅游
Tibet Travel
西藏旅游目的地 
走进神秘西藏
西藏风光图库 
热门点击